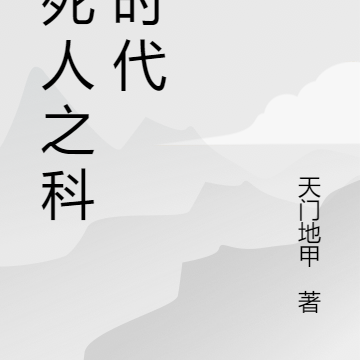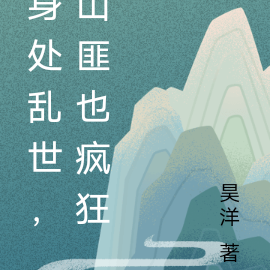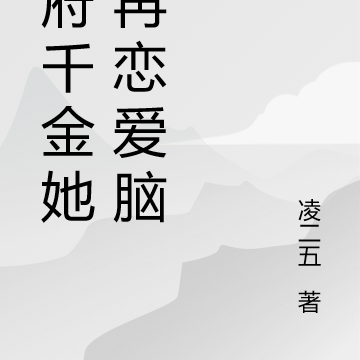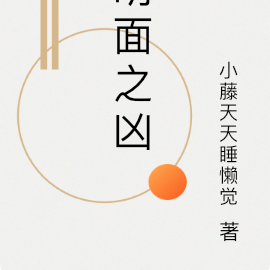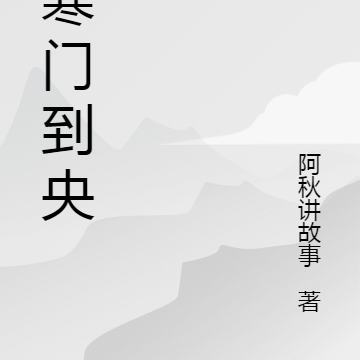救命我變成貓了提示您:看後求收藏(繁體小說www.fantilab.com),接著再看更方便。
夏朝已制定刑罰。《左傳·昭公六年》雲:“夏有亂政,而作禹刑。”《史記·夏本紀》所載《甘誓》,對軍隊的刑罰有具體闡述。“用命,賞於祖。”集解引孔安國曰:“天子親征,必載遷廟之祖主行。有功即賞祖主前,示不專也。”“不用命,僇於社。”集解引孔安國曰;“又載社主,謂之社事。奔北,則僇之社主前。社主陰,陰主殺也。”“子則帑僇女。”集解引孔安國曰:“非但止身,辱及女子,言恥累也。”
夏朝的法制指導思想可概況為奉“天”罪罰。奉“天”罪罰的法制觀表現為:一方面統治者的統治依據來自於天命;另一方面打著天的旗號實現統治。
夏朝穩定之後,為於調整社會關係需要,逐步形成和不斷擴充的。其基本內容是以制裁違法犯罪行為的刑事法律性質的習慣法為主,制定了《禹刑》,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部正規法典。
《唐律疏議·名例律》中有,夏刑三千條,鄭玄注《周禮》說:“大辟二百,臏闢三百,宮闢五百,劓墨各千。”可見夏朝法律數量應較多,規定應該比較細密,法制應初具規模。《左傳·昭公六年》載“夏有亂政,而作禹刑”。後人大多將《禹刑》作為夏朝法律的總稱。夏朝已初步形成五刑,並有一些罪名及定罪量刑的基本原則。
古文獻記載夏時期已具備較完善的刑法制度。《尚書·呂刑》中說道“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”,便是指周穆王將夏朝的《贖刑》作為制定周國刑法制度—《呂刑》的重要參考。而文中提到的《贖刑》很可能與《左傳》“夏有亂政,而作禹刑”的《禹刑》實為一物。
然《贖刑》、《禹刑》是否為夏之刑法,具體內容如何,已無可考。《左傳》中引述《夏書》中關於夏時刑法載“昏、墨、賊,殺”,指觸犯昏、墨、賊這三種罪過的人要判死刑。晉國叔向稱這種刑法為“皋陶之刑”。雖然死刑觀念應在新石器時代早已產生,但禹的理官皋陶可能是第一個將死刑法律化的人物。
夏朝有監獄。《史記·夏本紀》雲,桀“乃召湯而囚之夏臺,已而釋之。”索引曰:“獄名”。夏後槐的“圜土”、商湯被夏桀囚禁的“夏臺”便是夏時的監獄,為中國史書記錄最早的監獄。圜土是一種原始的監獄,在地下刨挖圓形的土牢,在地上搭架籬笆圈圍土牢。
《大禹謨》謂“戒之用休,董之用威,勸之以《九歌》,俾勿壞”,評價夏後立刑法是對民眾進行治理的一種手段。除了《禹刑》外,還有《政典》。
夏朝的軍隊,是為了維護統治而發明的專職征戰的工具。夏以前,各部落、部落聯盟之間的征戰由部落內部的青壯年男子負擔,夏建立後,中原形成了統一的部落共同體,並出現了國家機構,因此專職戰鬥的隊伍的建立是必不可少的。
禹徵三苗,稱他所統領的軍隊為“濟濟有眾”;啟徵有扈氏,嚴厲告誡所屬的軍隊要嚴格聽從他的指揮。足見當時已有強大的軍隊。《幹誓》是中國古代最早的軍法。
夏朝統治者為維護奴隸主貴族的利益,建立了一支奴隸主軍隊,於是原始形態的兵制也隨之產生。夏朝軍隊由夏王掌握。在確立啟的統治地位的甘之戰中(甘在今陝西戶縣西),啟要求全體參戰者要嚴格執行命令,對勇敢作戰、執行命令的人給予獎勵,反之則予以懲罰。
據《尚書·甘誓》記載:“用命,賞於祖;弗用命,戮於社,予則孥戮汝。”可見,夏朝的軍隊已經有嚴格的紀律。由於夏朝處在階級社會早期,生產力還不是很發達,因而夏朝的軍隊數量不多。例如,夏五世國王少康逃亡到有虞氏時,住在綸(今河南虞城東南),只有500部屬。後來,少康聯合斟尋氏和斟灌氏兩個部落,推翻了竊據夏朝的寒浞,恢復了夏王朝的統治。
夏朝軍隊的組織形式,在啟討伐有扈氏時,於甘地誓師所作的誓詞中,可略見端倪。《史記·夏本紀》雲:“將戰,作《甘誓》,乃召六卿申之。啟曰:‘嗟!六事之人,予誓告汝:有扈氏威侮五行,怠棄三正,天用剿絕其命。
今予維共行天之罰。左不攻於左,右不攻於右,汝不共命。御非其馬之政,汝不共命。用命,賞於祖;不用命,僇於社,子則帑僇女。’遂滅有扈氏。天下鹹朝。”
這段話的意思是說,啟在戰爭開始之前,召集臣屬,聲討有扈氏的罪行,並告誡將士,要忠於職守。立功者賞,違命者嚴懲不貸。啟滅有扈氏之後,諸侯皆臣服。誓詞中提及的六卿、六事之人、左、右、御等,皆軍隊將士的稱謂。
“六卿”,《史記·夏本紀》集解引孔安國曰:“天子六軍,其將皆命卿也。”“六事之人”,集解引孔安國曰:“各有軍事,故曰六事。”“左”、“右”,集解引鄭玄曰:“左,車左。右,車右。”“御”,集解引孔安國曰:“御以正馬為政也。”